沈满洪:浙商在践行“两山”理念的过程中,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故事 | 独家专访
2025-08-07 10:15:06 世界浙商
8月7日下午,“美丽中国与可持续的世界竞争力——2025浙商践行‘两山’理念20年论道”将在杭州拉开帷幕。
作为本次论道的特邀嘉宾,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、浙江农林大学原党委书记、宁波大学原校长沈满洪将出席活动并以《“两山”理念的理论逻辑及浙江实践》为题发表主旨演。在活动开始前,《浙商》杂志在杭州专访沈满洪,全面了解这位学术大家的人生、科研理经历及对“两山”理念的最新思考。

沈满洪
教授、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、浙江农林大学原党委书记、宁波大学原校长、浙江省第七批特级专家、浙江省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特聘专家委员。
您出身于浙江农村,现已成为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知名学者。现在看来,您觉得哪个节点的选择至关重要?
答:关键节点,是我在读研时进入了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。我本科学的是化学,毕业以后在高校工作,当时高校的博士化趋势越来越明显,所以我要读研究生。1994年,导师组帮我确定的方向是环境经济学。2002年,习近平同志从福建到浙江工作后很快提出了“生态省建设”,我就要帮助省里编制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,那时我已经积累了整整八年时间,有能力参与进去。所以,如果没有读研时的积累,我可能就是一个专职的政工干部了。但后来,我成为一个“双肩挑”,既当干部又当专家。

“水哥”“海叔”“碳翁”,您曾形象地把自己在专业领域的探索划分为这三个阶段?
答:是的。我做资源环境经济学一开始主要聚焦于水,做水资源、水生态、水环境领域的研究,都是围绕水的问题,所以我当时号称“水哥”。
到宁波大学工作以后,我觉得,如果一个综合性大学没有自己的学科特色,是很难脱颖而出的。宁波大学在海边,我希望能推进学校的学科建设的海洋化。一开始推不动,我就带头转型,后来转成功了,申请了一个关于海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,建立了海洋生态经济专业委员会,主编了海洋生态经济学的教材。所以那个时候号称“海叔”。
后来我到浙江农林大学以后,那里的许多研究跟碳汇紧密相关,再加上国家层面也提出了“3060”目标,也就是碳达峰、碳中和的目标。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比较聚焦的做碳中和研究。当然,这三者并不是完全简单的分割的,现在我对这三个方面也都有关注。
1994年时,整个社会对生态保护的关注还不多,为什么导师建议您选择这个方向?
答:导师的建议主要基于我本科学的是化学,因为搞环境经济学要了解化学方面的基础知识,我有这样的知识就比较轻松。当时,老师给我定的大方向是环境经济学,我自己的硕士论文是做环境经济制度研究,这跟当时的背景有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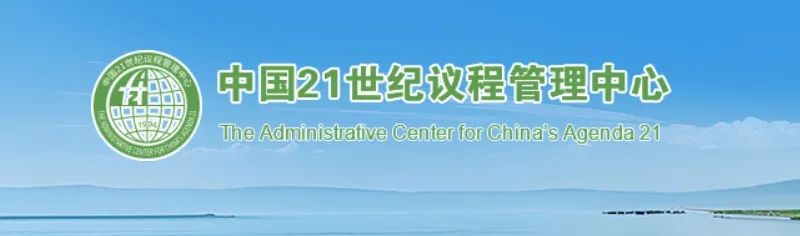
1992年,联合国环境大会通过了两个文件,一个是《21世纪议程》,一个是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。国际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是高度关注。1994年,国务院推出了《中国21世纪议程》,鼓励用经济手段保护环境,所以我就选择了环境经济制度研究,它主要的意图就是怎么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实现环境保护效果,因为环境保护不能不惜一切代价,要做成本收益的比较。
今年是“两山”理念提出20周年,它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?
答: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讲,现在浙江已经初步打造成一个“大花园”。现在,到我们的乡村和城市去看,生态环境的美丽程度已经是不亚于欧美的国家。
从生态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,我们呈现出了蓬勃的生机。同时,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、城乡统筹、城乡融合发展等都有关系。“两山”理念的践行把生态产品转变成经济价值,跟这个事情也是有关的。现在,生态环境的保护、生态经济的发展、生态共富的推进在全国呈现出很好的趋势,给全国都带来了绿色福利。这样的中国理念、中国方案、中国实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,应该说“两山”理念作为指导思想,充分显示出了它的真理伟力。
很多企业做这个绿色转型的时候,会不会付出比较大的代价?
答:“两山”理念的践行主要是两个方面,一方面是经济生态化,另一个方面是生态经济化。我们只有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走绿色化、生态化的道路,才有可能守得住优美的绿水青山。同时,绿水青山中的一部分作为生态功能,本来就是普惠的,金不换的。

浙江企业在践行“两山”理念的过程当中,涌现出以天能集团为代表的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故事。技术的突破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,一旦突破,那就是换了一片天地。所以浙江的企业在经济生态化的过程当中,有一种壮士断腕的精神和境界。特别可贵的是,他们善于利用市场机制,把生态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。两山的转化最关键、最根本还是要利用生态优势发展生态产业。生态产业靠谁发展?主要靠的是企业、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。
在企业家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外,地方政府应当起到哪些作用?
答:在经济体制改革、市场化改革、环境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当中,浙江始终走在全国前列。浙江省委和省政府在“两山”理念转化的过程当中,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,这一点是特别宝贵的。
从2005年起,浙江就从全省范围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制度,后来新安江流域的共建、共保、共享,又是全国第一个跨界流域的生态补偿。现在,跨界流域的生态补偿已经走向了全国,连长江黄河这样的大江大河都已经建立起了跨界生态补偿机制。
所以,浙江省委省政府以及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市场环境的营造方面,生态文明制度的供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,正是因为制度环境做的特别好,才保障了浙江企业既能够做到经济生态化,又能够做到生态经济化。
下一个20年,您对浙商更好的践行“两山”理念有哪些建议?
答:面向未来,随着我们现代化国家的建设,收入水平的提高,老百姓对优质的生态环境、优质的生态产品、优质的生态服务的期望会不断提高。对企业家来讲,谁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生态产品,谁就能够抓住这个机会。
但也面临着一种挑战,因为政府对环保的标准要求也越来越高,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生态保护、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,呈现出跟西方发达国家不太一样的路径。西方发达国家是先污染后治理,而中国是面临着工业化、绿色化、低碳化“三化并举”的状态。这意味着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一定要有非常规的创新举措,才有可能在机遇面前抓住机遇,才能够在约束条件下实现绿色利润的最大化。
您之前提到过一个观点,“生态科技是实现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法宝”。浙商在绿色技术创新上可以有哪些发力的方向?
答:浙商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事光伏发电、风力发电等新能源开发的。
我们的企业家厉害到什么程度?我2010年在内蒙古调研的时候,光伏发电的成本是1.1元,风力发电是0.58元,内蒙古的火力发电只要0.16元。当时我很悲观,我们的新能源何时才能够走向市场?但到了2015年,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降到了0.5元以下,2020年降到了0.3元以下。
我们的企业能做到从生态不经济转向既生态又经济,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。所以说企业家有两种精神,一种是冒险精神。十几年前进入到光伏行业,那是要冒险的。另外一个精神就是创新精神,创新精神既包括科技创新,也包括企业内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,其中科技创新是最关键的。
您之前还提到一个观点,之前我们是“非绿色发展”,后来是“浅绿色发展”,接下来我们要迈向“深绿色发展”。您对“深绿色发展”的界定是什么?
答:一段时间以来,在这个工业化过程当中,我们也经历过了以高投入、高消耗、高排放为代价的高增长。我们不能否定这个过程做出的重要贡献,但一定要看到,这背后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很大,这样一种粗放式的增长方式,我们称之为“非绿色增长”。
后来我们越来越重视资源节约、环境保护,提出了科学发展观、生态文明、美丽中国建设。在大政方针的领导下,我们的企业逐渐向绿色发展转型。但是这个绿色发展还没有能够做到从源头上完全控制住。往往是有了污染的排放,企业先治理,治理到达标再排放,这样的一种方式总体上可以称之为“浅绿色发展”。
“深绿色发展”,要在源头上就解决污染问题。在生产的过程如果有排放,要及时收集那些废弃物,能够循环的产品,报废以后又要回到输入端,建立起真正的循环经济链条。所谓零碳、零废城市的建设就是这样的目标。目前,我们已经完成了从“非绿色发展”到“浅绿色发展”,从浅绿色发展到深绿色发展还在推进的过程当中。可喜的是,我们已经看到深绿色发展的样本越来越多,工业领域也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案例。
您对“美丽中国与可持续的世界竞争力——2025浙商践行‘两山’理念20年论道”活动有哪些期待?
答: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。在推动绿色发展、美丽中国、美丽浙江建设的过程当中,政府起主导作用。因为无论是战略的谋划,规划的编制,制度的供给都是由政府来承担的。这些东西完成以后谁来做呢?企业是一个重要的主体,只有企业家认识到了“两山”理念的重要性,绿色发展的重要性,才可以转变成企业的具体实践。公众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,因为公众参与既可以监督政府的行为,又可以监督企业的行为。
多年来,浙商不仅在以经济体制改革、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当中勇立潮头,在未来的深绿色发展过程中,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中也能够勇立潮头,我们这个活动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助推作用。
来源:《浙商》杂志 记者 胡淼
